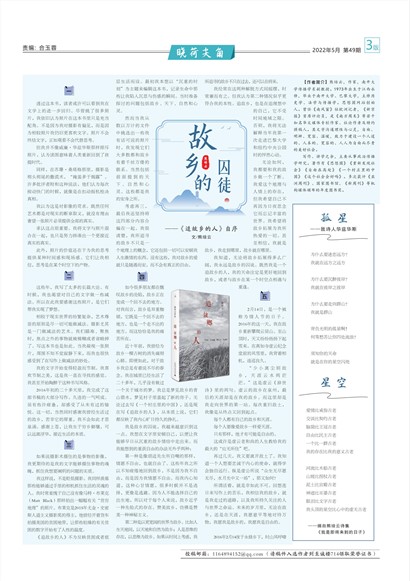故乡的囚徒
——《追故乡的人》自序
1
透过这本书,读者或许可以看到我在文学上的进一步回归。尽管挑了很多照片,我依旧认为照片在这本书里只是充当配角。不是因为我对摄影有偏见,而是因为相较照片我仍旧更喜欢文字。照片不会终结文字,正如观看不会代替思考。
但我并不像威廉·华兹华斯那样排斥照片,认为读图意味着人类重新回到了孩提时代。
同样,在苏珊·桑塔格那里,摄影是彻头彻尾的撒谎术,“掩盖多于揭露”。许多批评者附和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每次按动快门的时候,就像是在扣动扳机枪决真相。
我以为这是对影像的苛求。既然任何艺术都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就没有理由奢望一张照片必须提供全部的真实。
承认这点很重要。我将文字与照片混合在一起,也只是努力拼凑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真实。
此外,照片的价值还在于为我的思考提供某种时间感和现场感。它们让我相信,思考是在某个时空下的产物。
2
这些年,我写了太多的长篇大论。有时候,我也渴望对自己的文字做一些减法。所以在此我要感谢这些照片,是它们帮我实现了梦想。
相较于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艺术尊崇的原则是尽一切可能做减法。摄影尤其是一门做减法的艺术。我们瞄准、聚焦时,焦点之外的事物就被模糊或者省略掉了。写这本书也是如此。当我凝视一张照片,周围不知不觉寂静下来,而我也很快感受到了在写作上做减法的妙处。
我的文字开始变得轻盈而节制。我喜欢节制之美,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感觉。我甚至开始陶醉于这种书写风格。
2016年初的二十多天里,我完成了这部书稿的大部分写作。久违的一气呵成。虽有些许疲惫,却感受了从未有过的愉悦。这一切,当然同时感谢我曾经生活过的故乡,若非它的厚重,我不会如此才思泉涌。感谢上苍,让我生于穷乡僻壤,可以远离浮华,接近生活的本质。
3
如果说摄影术摄住的是事物的影像,我更期待的是我的文字能够摄住事物的魂魄,抓住我想要阐明的问题的实质。
我这样说,不是贬低摄影。我同样羡慕那些能够通过手里的相机抓住生活的灵魂的人。我时常羞愧于自己没有像马特·布莱克(Matt Black)那样拍出一幅幅有关“贫穷地理”的照片。布莱克是2015年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得主,他曾经开着货车拍摄美国的贫困地带,让那些枯燥的有关贫困的数字开始有了人性的温度。
《追故乡的人》不为反映贫困或者底层生活而设。最初我本想以“沉重的时刻”为主题来编辑这本书,记录生命中那些让我陷入沉思与伤感的瞬间。当时准备探讨的问题包括故乡、天下、自然和心灵。
然而当我从数以万计的文件中挑选出一些我有话可说的照片时,我发现它们大多数都和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包括前面提到的天下、自然和心灵。这些都是我的安身之所。
考虑再三,最后我还坚持将这四部分内容合编在一起。我很清楚,我所追寻的故乡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它还包括一切可以安顿我人生激情的东西。没有这些,我对故乡的爱就只是随遇而安,而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4
如今很多朋友都在慨叹故乡的沦陷,故乡正在变成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对我而言,故乡是双重枷锁,它既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也是一个走不出的地方。而这恰恰是我的痛苦所在。
近十年前,我曾经为故乡一棵古树的消失痛彻心肺。即便如此,对于故乡我总是有着说不尽的眷念。我在城里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几乎没有做过一个关于城市的梦。我总是梦见故乡的青山碧水,梦见村子里盖起了新的房子。无论过去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还是现在写《追故乡的人》,从本质上说,它们都反映了我内心旷日持久的挣扎。
我是故乡的囚徒,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我想在文字里安顿自己,以便让我能够早日从沉重的故乡情结中走出来。而我能想到的重获自由的办法无外乎两种:
第一种是像胡适先生所自嘲的那样,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些年我之所以不知疲倦地回到故乡,不是因为我不自由,而是因为我情愿不自由。而我内心知道,这种心甘情愿,很多时候并不是选择,更像是逃避。因为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所以对于每个人来说,故乡近乎一种先验式的存在。赞美故乡,仿佛是赞美一种神秘主义。
第二种是以更宽阔的世界为故乡。比如人生天地间,以天地和自然为故乡;人是思维的存在,以思维为故乡。如果从时间上考虑,我所追寻的故乡不只在过去,还可以在将来。
我经常在这两种解脱方式间摇摆,时常兼而有之。但我认为第二种情况似乎更符合我的本性。追故乡,也是在追理想中的自己,它不受时间地域之限。否则,我将无法解释当年我第一次走进巴黎大学和纽约中央公园时的怦然心动。
无论如何,我都要和我的故乡做一个了断。我爱这个地理与人情上的存在,但我希望自己不再因为日夜思念它而忘记丰富的世界。我希望将故乡拓展为我所热爱的一切。甚至相信,我就是故乡,我走到哪里,故乡就在哪里。
我知道,无论将故乡拓展得多么广阔,我永远是故乡的囚徒。既然我是一个追故乡的人,我的天命注定是更好地回到故乡,或者与故乡在某一个时空点相遇与重逢。
5
2月14日,是一个被称为情人节的日子。2016年的这一天,我在故乡重新攀爬云居山。至山顶时,天又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在真如寺虚云纪念堂前的风雪里,我背着相机,逡巡良久。
“少小离尘别故乡,天涯云水两茫茫。”这是虚云《辞世诗》里的两句。虚云的故乡在泉州,最后的天涯却是在我的故乡。而这里却是我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每次重归故土,我像是从终点又回到起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和天涯。
每个人要像爱故乡一样爱天涯。
只有那样,他才有可能是自由的。
这或许是虚云老和尚的人生教给我的最大的“应无所住”吧。
再过几天,我又要离开故土了。我知道一个人想要忠诚于内心的使命,就得学会独自远行。纵是虚公所说“众生无尽愿无尽,水月光中又一场”,那又如何?
所谓活着,就是非如此不可。回想连日来写作上的苦乐,我相信我的故乡,就是我走过的道路,以及我所持久关注的人与世界之命运。未来的岁月里,无论在故乡,还是在天涯,我愿意平等地对待万物,我愿我是故乡的,我愿我是自由的。
2016年2月14夜于永修乡下,时山风呼啸
【作者简介】熊培云,作家,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1973年出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曾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是《南方周末》等若干知名华文媒体专栏作家、社论作者及特约撰稿人。其文字沟通理性与心灵,自由、明辨、宽容、温暖,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人人为自由而尽责的美好社会。
写作、讲学之余,主要从事政治传播学研究。著作有《思想国》《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个社会会好吗》。多次获评《亚洲周刊》、国家图书馆、《新周刊》等机构媒体颁布的年度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