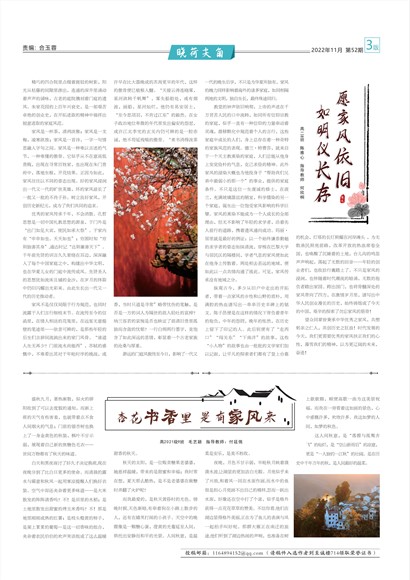愿家风依旧,如明仪长存
精巧的四合院里点缀着斑驳的树影,阳光从枯藤的间隙里渗出,连通的深井里涌动着声声的诵咏,古老的庭院镌刻着门庭的遗风。朱家花园的上百年兴衰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创业史,在开拓进取的精神中徜徉出锐意进取的家庭风范。
家风是一杯茶,清冽淡雅;家风是一支梅,凌寒欲放;家风是一首诗,一字一句情思融入字句之间。家风是一种难以言述的气节,一种难懂的傲骨。它似乎从不在意高低贵贱,出现在寻常百姓家,也出现在朱门贵府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家风往往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好的家风浸润出一代又一代的旷世英雄,坏的家风滋长了一批又一批的不肖子孙。树立良好家风,开创历史新纪元,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追求。
优秀的家风传承千年,不会消散。孔哲思想是一切中国礼教思想的源泉,于门外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于家内有“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穷困时知“穷则独善其身”,通达时记“达则兼善天下”。千年前先贤的训言久久萦绕在耳边,深深融入了每个中国家庭之中,构建出中华文明,也在华夏儿女的门庭中流传成风。先贤圣人的思想犹如流床且铺的金沙,在岁月的择取中仍旧闪耀出光彩来。由此生长出一代又一代的历史推动者。
家风不是仅仅局限于行为规范,也同时流露于人们言行细枝末节。在流传至今的信函里,在情人相送的花笺里,在远客无意提壁的笔迹里……依昔可辨的,是那些年轻的后生们言辞间流淌出来的家门风骨。“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苏轼的感慨中,不难看出其对于年轮时序的挑战,或许早在比大器晚成的苏洵更早的年代,这样的傲骨便已植根入髓。“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雾失船舫处,或有烟波,画船,星河灿烂,他仍有易安居士,“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毅然。在女子政治地位卑微的年代里发出偏安的怨怼,或许江北李宅的玄关内仍可辨的是一腔赤诚,绝不苟延残喘的傲骨。“煮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略带忧伤的笔触,是否是一方的词人为隔世的故人轻吐的哀掉?纳兰容若的哀惋是否也映证了前清旧贵里孤独而含敛的忧郁?一行白绢两行墨字,竞饱含了如此深远的思情,彰显着一个古老家族的沧桑与厚重。
渺远的门庭风貌传至今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晚生后学,不只是为华夏所独有,家风的魄力同样影响着海外的诸多家庭,如同相隔两地的文明,独自生长,最终殊途同归。
教堂的钟声依旧响彻,上帝的声述在千万贫苦人民的口中流转,如同所有信仰宗教的家庭,似乎一直有一种信仰的力量牵动着灵魂,潜移默化中规范着个人的言行,这些家庭中成长的人们,身上总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家族风范的表现。德兰·特曹莎,就来自于一个天主教熏染的家庭,人们总能从他身上发觉俭朴的气息,克己求俭的精神。此外家风的浸染大概也为他投身于“帮助我们兄弟中最弱小的那一个”的事业,提供的家庭条件。不只是这位一生虔诚的修士,在波兰,充满玻璃器皿的陋室,科学儒染的另一个家庭,诞生出一位饱受家风影响的科学巨擘。家风的熏染不能成为一个人成长的全部理由,但无不影响了年轻的求学者,沿着先人前行的道路,携着遗风通向成功。玛丽·居里就是最好的例证:以一个始终谦恭勤勉的求学者的姿态如抹清流,穿梭在巴黎大学与居民区的隔楼间,学者气息的家风便如此在他身上传散着。两处相去甚远的地域,便如此以一点共情沟通了彼此。可见,家风传承没有地域之分。
纵观古今,多少从旧户中走出的开拓者,带着一点家风的乡性和山野的质朴,用满腔的热血谱写出一串串历史丰碑上的铭文。陈子昂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背负着青年的抱负,中年的怨罔,晚年的怅然,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的人。此后别便有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的故事,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也由一批批的文学家们加以记叙,让平凡的探索者们都有了登上台慕的机会,灯塔的长灯照耀在河岸滩头 ,为无数渔民照亮前路,改革开放的热浪席卷全国,也唤醒了沉睡着的土地,台儿沟的鸣笛声声响起,荡起了无数的回音……年轻的创业者们,也收拾行囊踏上了。不只是家风的浸润,也伴随着时代潮流的暗涌,无数的抱负者踏出家园、跨出国门,也将骨髓深处的家风带向了四方,在激情岁月里,谱写出中华人民创业漫长的历史,始终铸熔成了今天的中国,艰辛的探索了勿忘家风的筋骨!
望众同辈皆秉承中华优秀之家风,共塑躬亲之仁人,共创历史之狂浪!时代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优秀的家风扶正我们的心性,藻雪我们的精神,以为更辽阔的未来,奋进!